编者按:又是一年高考时,苦涩又充满希望的高考岁月令每个人刻骨铭心。时至今日,高考仍然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一环,是青春学子通往美好未来的最公平道路。如果没有高考,以下这8位顶级企业家也许就没有今日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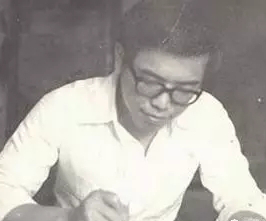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从北京传到千里之外的广东省惠阳县马安农场,那时下乡知青李东生刚过完20岁生日。不经意间,他已经在疲倦而枯燥的田间地头耕耘了三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不能在农场待一辈子,我要尽快出去,我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个愿望一直是比较清楚的。”
老天爷似乎想考验一下渴望春天的年轻人,这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李东生所在农场的知青被调去参加挖水库的大会战,他回忆说:“外面在刮大风,在工地上住着一个茅棚,茅棚里面就刮小风。茅棚没有电,就点一个煤油灯,在那里看书,为了让煤油灯亮一点,我们用纸卷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火苗可以大一些,亮一些。这样看书,很艰苦,很艰苦。”此时距离高考仅两个月,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农场规定所有人不许请假复习,李东生只得晚上点煤油灯学习,周末骑自行车到城里找高中老师辅导。
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尽管李东生鼓足勇气,却难免紧张,考场是一间狭小逼仄的教室,“骨瘦如柴”的课桌看起来十分脆弱,他谨小慎微,总担心稍稍用力就会把桌子压垮。
1978年春天,李东生以物理、化学考分惠阳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录取,也是当年全农场50多名知青中惟一考上大学的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李东生成为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一员。
“50177”是无线电专业的代号,两个班一共80名学生,年纪最大的40岁,最小的18岁,然而,相差12岁的人同窗学习并非稀奇,而是当年大学校园的普遍景致。不过,堪称特例的是,后来威震中国家电行业的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康佳集团掌门人陈伟荣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三人均出自同一个班,绝无仅有;鼎盛之时,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故而被业界称为“华工三剑客”。
三人年纪相仿,关系颇为不错,据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黄宏生是穿着露出大脚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校的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陈伟荣最小,生于1959年,不过在同学们看来,与另两位哥们儿一样,没人料到他们后来会当上大老板。
身为学习委员,李东生勤奋刻苦的学习劲头丝毫不逊于班长黄宏生。那时学校每周都会放一场电影,除非名气特别大或特别想看的,一般情况下李东生都视而不见,他说:“我觉的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情,有时间应该学习。”在那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月,尽管花样年华,但埋首苦读的校园生活毕竟单调枯燥,与之相比,“华工三剑客”日后在家电江湖中的恩怨情仇显得荡气回肠,精彩纷呈。在往后的叙述中,读者将看到三位昔日同窗好友既有相濡以沫的温情,也有同室操戈的残忍,商战烟云,令人唏嘘。
1981年,李东生步入大三,即将毕业。这一年,他的家乡惠州诞生一家合资企业,在当时看来,此事与毫无瓜葛,毕竟他属于凤毛麟角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不可能被分配此处。
可命运总是无法捉摸,一如1977年的那场高考,谁能预料?

马云上大学可谓一波三折,历经三次高考,侥幸过关。
1982年,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理想是北京大学,但是成绩出来后惨不忍睹,数学只考了1分。马云深受打击,打算去做临时工,就和高大帅气的表弟去一家宾馆应聘,结果表弟成功上岗他却遭到拒绝。后来他做过秘书,当过搬运工,又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山海经》、《东海》、《江南》杂志社蹬三轮车送书。25本书刊捆成一包,他骑10公里路通过火车渠道发到全国各地。有一天,他偶然得到帮浙江舞蹈家协会主席抄写文件的机会,在这里第一次路遥当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代表作《人生》。受书中主人公高加林的影响,马云重新燃起斗志,报名参加第二次高考。
遗憾的是,他这次又落榜了,数学考了19分,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40分,连父母都对他不抱希望。那时候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正风靡大江南北,主角小鹿纯子甜美的微笑迷住一代人,马云深受她永不言败的精神所鼓舞,鼓起勇气,准备第三次高考。多年以后,2003年“非典”过后,小鹿纯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到访阿里巴巴,马云也算圆了当年的追星梦。不过,由于家人反对,1983年他只好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每周日早起一小时赶到浙江大学图书馆复习。
第三次高考,老天爷似乎不忍心再折磨这个“阿甘”式的学生,马云的运气出奇的好。考数学的那天早上他背了10条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时10条公式逐条套用,结果考了79分。可惜,他离本科分数线还差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的专科录取。哪想到学校外语系本科生名额未招满,他被调剂进入外语系本科专业。
三次高考才靠运气勉强进入他自己所说的“最差的大学”,马云提前体会到屡战屡败的滋味,也修炼出永不言败的气质,他说:正因为我从普通家庭出来,从普通学校出来,高考也失败,我才特别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和市场客户小老板的心态,我又学的是英文,所以我知道西方社会里倡导的是什么。”
比别人幸运的是,虽然生长于普通家庭,但马云在大学期间得到一次出国学习的机会。这段故事源于他十五岁那年,因为想练英语,经常跑到外国游客聚集的地方主动与人搭话,免费当导游,因此结识来自澳大利亚的摩利夫妇。马云和摩利夫妇非常投缘,一直保持长久的交往。马云读大二这年,摩利夫妇邀请他去澳大利亚游玩,走出国门,好似整个世界都对马云敞开大门,一切都豁然开朗,他慢慢学会以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人生和世界。
大学期间,马云的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不太用功也能位居前五名。他对学业并不上心,却热衷参加学校社团活动,连周边高校的一些男生都认识他。大三这年他当选校学生会主席,并以舍我其谁的霸气当选杭州市学联主席,把校园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每天激情澎湃的东奔西跑,一份油印的校报描写当时的马云:“咬一咬牙,他骑的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多年后马云回忆大学生活时说:“我自己觉得,算,算不过人家;说,说不过人家。但是我大学过得很成功,创业也成功了——如果马云能够成功,我相信80%的人都能成功。”

1984年对于俞敏洪而言,是失落而苦闷的一年。这年7月,他应该与同学一起毕业,共奔前程,然而,因为患病而休学一年,晚一年毕业,他只能目送同学们离别的背影,转身时满脸落寞。
俞敏洪经过三次高考才考上大学。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英语只考了33分,名落孙山;第二年,他再次参加高考,英语考了55分,再度落榜。两度高考失利对俞敏洪打击很大,同村跟他一样两次高考失败的一个同学已经决定在家务农了,想到未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对父母说:“我想再考一次。”这一次,俞敏洪考上了北京大学。
持之以恒、坚定执著的俞敏洪终于实现理想,这还得感谢英语老师的鼓励。“任何年代,只要考上大学,就会由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咱农村人最坚定的梦想就是死也要成为城里人,”老师当年的话俞敏洪记忆犹新,“我们班的同学全都参加了高考,没人放弃,即使没有考上大学,将来种地的时候,也会自豪地说曾经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后来我热爱英语,和对这位老师的崇敬密切相关。”
高考分数出来后,俞敏洪超过北大录取分数线7分,但他不敢填报,很多比他分数高的同学都没敢填北大,还是老师替他在“第一志愿”写下“北京大学”四个字。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俞敏洪仰天大笑,然后痛哭流涕,那情景与“范进中举”别无二致。
1980年9月,俞敏洪穿着打了补丁的白衣蓝裤,挑着扁担,背起行囊,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到北大西语系报到。进入燕园,俞敏洪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新鲜,可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也让他清醒,同学们都穿着得体,脸色白净,而他一身泥土气息,显得太另类。满脑子“天之骄子”的自豪感顿时烟消云散,俞敏洪第一次感到自卑,打击就此开始。
俞敏洪的班上只有他一个人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最差,因此,他的穿着常被人嘲笑,“大补丁”的绰号不胫而走。上体育课时,老师会吼一嗓子:“大补丁,来做个动作。”每到此时,都会引起在场所有人哄堂大笑,俞敏洪脸臊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在北大的五年间,俞敏洪过得非常煎熬,屡遭打击,经常没有尊严,更谈不上浪漫。刚开始听说班上50人男女性别比“一比一”,俞敏洪非常兴奋,可是五年下来,没有一个女生拿正眼看他。
大三这年,俞敏间歇性咳血,医生告诉他患有肺结核。因为患病休学,俞敏洪只好从1980级转到1981级,悲哀的是,聚会时两届同学互相问候,却没有一个人看望俞敏洪,大家都认为俞敏洪不是自己的同学。这让极度敏感的俞敏洪感到悲伤辛酸。痊愈之后,由于服药过多导致血液浓度改变,俞敏洪脸上布满疮疤,这让他更加自卑,直到毕业都少言寡语,形单影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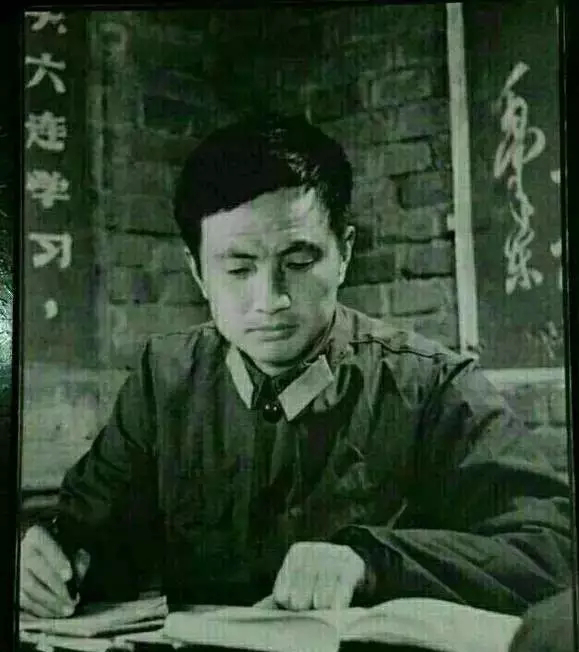
任正非的文采在企业界人尽皆知,他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怀念长文《我的父亲母亲》,据说发表前还叮嘱下属不准擅自改动一字。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任摩逊在抗战时期是一名热血青年,后来进入广州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任会计,为躲避战乱随厂迁至贵州。在此期间,任摩逊与程远昭结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家中长子。解放后任摩逊长期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程远昭自学成才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仅靠夫妻二人当老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全家9口人何其艰难,任正非回忆道:“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高三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备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我无以报答他们。”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上大学任正非得单独拿走一条,可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
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三门外语。
第二年6月,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继续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加入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
时至今日,任正非仍然是中国最低调的企业家,“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任正非说,“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如此低调孤独,以致任正非本人和华为成为中国企业界谜一样的存在,难怪被人称作“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伴随“小米”迅速崛起之后累积的巨大声誉,雷军已经家喻户晓。
1969年12月16日,雷军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剅河镇赵湾村,地处江汉平原中部排湖北岸。9岁那年,雷军全家迁往县城居住,他本人插班进入建设街小学读书,直到5年级毕业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学校给他戴上“三好学生”的大红花,细心如发的母亲一直将他佩戴大红花的照片珍藏至今,记录他勤奋好学的点滴过往。
1984年,雷军从沔阳师范附属学校初中毕业,考入当地最好的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这所学校每年为全国高校输送上千名优秀人才。雷军在中学时非常喜欢下围棋,曾获得学校围棋冠军。他也喜欢文学,经常阅读《小说月报》,对古诗词尤为钟爱,唐后主李煜是他最喜欢的词人。不过他并未玩物丧志,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前几位,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
1987年9月,雷军的高考成绩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分线数 10 分,却拿着上清华、北大“门票”步入武汉大学,开始四年的大学岁月。为了能坐到最好的位置,每天7点,晨光初露,雷军就已经到教室占座位去了。周末他喜欢去看电影,但经要要自习到九、十点钟后去赶第二场。从小到大,雷军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可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上自习,他归结为“不自信”。
这一年,一本书让雷军找准梦想,他回忆说:“王川给我一本书。两块一本,《硅谷之火》。从此,乔布斯给了我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我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梦想。”《硅谷之火》讲述的是言论自由运动时期,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带来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那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激动人心创业故事,无一不成为一粒火种,彻底点燃了雷军的梦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乔帮助那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
大一学年结束,雷军成绩全年级第一。但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不比水平考试第一,计算机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没有实践,高分都是浮云,一切的一切只是高分低能、纸上谈兵。所以,从大二开始,他就经常上武汉电子一条街“混”技术去了。他经常背着个大包,在街上帮人装软件、修机器、编写程序。由于雷军勤学好动,慢慢地技术也越来越娴熟,街上很多老板都认识他,喜欢请他帮忙,经常请他吃饭,雷军在街上“混”得很不错。
武汉大学是国内最早实施学分制的高校,只要修完一定学分就可以毕业。雷军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虽是速成,但雷军的水平远远超出读四年的同学。二十年来,他是系里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满分成绩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射手座的雷军富有想象力,从小就喜爱诗歌,对写程序也特别有感觉,总是有意无意的像写诗一样写程序。雷军大一写的PASCAL程序,等他上大二的时候,这些作业都已经被编进大一教材。

1984年9月,郭广昌放弃了父母的安排,没有去金华师范学校(中师)报到,而是转读东阳中学。社会大环境正悄然改变,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下海”经商,郭广昌对未来也有更大的期待,而不仅仅满足于中师毕业后当老师端“铁饭碗”。父母对他的做法极力反对,他无法说服,就悄悄卷走一床竹席,背着十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上了东阳中学。
东阳中学是浙江省首批通过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郭广昌的入学成绩位于中下游,然而1984年升上高二之后,他的成绩即呈飙升趋势。据高中班主任吴加清老师回忆,郭广昌过得非常刻苦,非常清苦。
学校有一个藏书不多的小图书室,那些只顾埋首应付高考的同学很少把时间“浪费”在课外读物上,而郭广昌很喜欢学习一些课外知识。周末、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他却留在图书馆里读书。他对商业传奇和哲学类的书籍尤其感兴趣,往往一看就是数个小时。郭广昌中学之所以很少回家是因为路途遥远,回去要走四五个小时的崎岖山路,返回即便有家人用自行车送,也很麻烦。而且家里也没有多少地,他能帮忙干的农活有限,所以很少回家。他不得不回家的理由只有一个:背大米和带母亲做的霉干菜。东阳出了很多博士,霉干菜是当地读书人的必备 “食粮”,有“博士菜”之称。
1985年,郭广昌以史无前例的高分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他至今记得,踏入大学校门那一天,哲学系学长们迎接新生的欢迎辞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禅意十足的佛语充满入世情怀和献身精神,18岁的少年激动不已,豪情满怀,浑身涌动着大干一场创立基业的热血。
在复旦,郭广昌热爱哲学,却并没有死守哲学,他还选修物理和经济学。当然,泡图书馆的习惯他一直没放弃,在复旦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每天都有郭广昌如饥似渴饱读各类图书的身影。有人曾经专门去翻看过郭广昌当年的阅读记录,发现赫然记载着诸如《冶金原理》之类跟他的专业毫不相关的生涩专著。郭广昌说过,他的大学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学无专长的博学家,这种“杂食”喜好,冥冥注定复星集团多元化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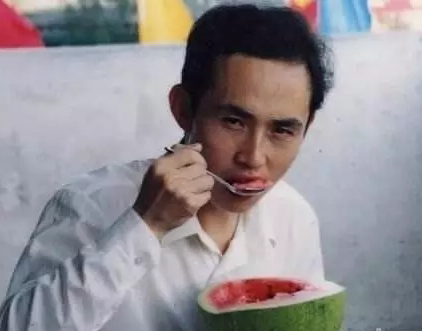
梅花香自苦寒来,贫穷与苦难一直是潘石屹命运的主旋律。
1963年,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天水潘集寨的一户农家。潘家祖上是书香门第,潘石屹的曾祖是清末秀才,爷爷毕业于黄埔军校,父亲曾经考上大学,家族极其重视教育,潘石屹就是在那种“穷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书”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尤其重视潘石屹的学习,虽然家里一直是揭不开锅的状态,但父亲还曾嘱咐潘石屹的姑姑给他买一套“毛选四卷”。潘石屹很争气,虽然经常帮父亲做一些体力活,但学习没有丝毫的耽误。
1977年秋天,潘诗麟得到平反,全家户口从农村调到城镇,家也搬到甘肃省清水县城,虽然日子依旧贫困,但县城的景象让潘石屹看到生活的希望,也让他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1979年,潘石屹报名参加高考,很不幸,距离高考还有8天时出了车祸,被一辆卡车刮倒,肩胛骨被撞断,这直接导致他在高考中没能正常发挥。考试结束后,潘石屹琢磨,很多题没写出来,分数上不去,肯定与大学无缘。他灵机一动,到隔壁县以“石屹”这个名字参加中专考试,最终考入兰州培黎学校(中专),并且拿到年级第一的成绩。潘石屹的人生从此出现巨大转折。
1979年,16岁的潘石屹孤身一人离家前往省城兰州求学。他肩上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裹着他的所有家当——一件棉衣、一条裤子,手里攥着父亲用家里所有积蓄买来的火车票。望着儿子因为营养不良单薄瘦小的身影,直到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消失不见,潘石屹的父亲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潘石屹却精神亢奋,他整了整头上的帽子,这顶帽子是父亲的,不算太破旧,父亲用它换走潘石屹更破旧的帽子,虽然兜里没有一分钱,未来的日子怎么过也毫无头绪,潘石屹却坚信,美好的生活正在向他靠近。
当时学校食堂的饭是把杂粮和细粮搀和在一起的,很多来自城镇的女孩子吃不惯杂粮,每顿饭都会把杂粮剩下来,这些被挑出来的杂粮成了潘石屹很长一段时间的口粮。这种情景,与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读书经历何其相似。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潘石屹就这样度过大学生活。
两年后,潘石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石油管道学院,从中专升入大专,三年后,潘石屹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位于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成了局里经济改革研究室的一名小科员。

1961年10月20日,陈九霖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户贫困农家,父母先后生育六个孩子,只有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存活下来。母亲为抚养三个孩子辞任小学代课老师,全靠任公社书记的父亲养家糊口。文革期间父亲屡遭批斗,东躲西藏,举家借债度日,已无力供子女读书。陈九霖初中毕业不得不回乡担任英语代课老师,后来调到农村信用社工作。
农家子弟跳出农门只有两条出路:当兵或考大学。陈九霖曾顺利通过海军的体检、政审,就在入伍前夜,母亲因不舍离别在他面前哭成泪人,他毅然放弃从军,并扔掉信用社的铁饭碗,偷偷卷起铺盖逃到百公里外的罗田县骆驼坳中学读书。数日杳无音讯之后,母亲凭直觉辗转找到他,劝他转到教育质量更好的黄州中学就读。
陈九霖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并没有从高一开始读起。时间不等人,他找到英语老师卢祥福,请求破例直接插班到高三“英语加强班”。陈九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比班上其他同学付出更多努力。“因为只有初中的底子,陈九霖学外语好像就没有放下的时候,而且很好问,英语老师来了他不问几个问题决不罢休。”陈九霖的高中同学、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刘思源回忆。陈九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疯狂恶补落下的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九霖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取得非常优异的高考成绩,投入努力最大的英语考了88分。陈九霖如愿以偿,顺利被北京大学东语系录取。那年黄州中学全校的高考录取率还不到4%,学校通过陈遂祥去给儿子领录取通知书。当时陈遂祥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还以为别人在取笑父子之间的分歧。但是,当他亲手拿到那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整个人立刻笑得合不拢嘴。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录取通知书很大气、很大气。”他兴奋得几天都没睡着觉。
陈九霖考上北大不只是一家人的喜事,也是整个宝龙村的大喜事。他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大学生,被乡亲们夸作“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在陈九霖离开故乡前往北京的那天,全村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连隔壁邻村的村民都自发前来为陈九霖送行。他们买来大捆的鞭炮,在村里整整放了一个小时。
在热闹喧天的鞭炮声中,陈九霖提着一只大红色的行李箱,孤身一人离开小村庄,在浠水县竹瓦镇乘坐长途大巴到达省会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前往他梦里出现过千百次的北京。
从那一刻起,陈九霖彻底告别浠水,告别乡村,开始跌荡沉浮的无畏人生。
本文节选自陈润著作《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
(责任编辑 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