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制高点,世界商业发展史中一个奇峰突起的异数。
明清两代,山陕、徽州、山东、江浙、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陆续兴起一支支资本雄厚的地域商人集团,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主宰了中国商界风云近五百年。
晋商以贩盐起家,又以“票号”拉开了中国金融史上的辉煌一幕,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伟理想;徽商走出地瘠人稠的大山,贾而好儒,在商场及朝堂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粤商敢于冲破海禁,集资结帮从事长途贩运,从急风巨浪中博取巨富……诸多商帮各具特点,不仅留下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还固定了经理人制、合伙制、会计制等创新管理制度,在农耕文明的古老版图上开拓出现代商业的雏形。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从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第一是‘集权’,第二是‘抑商’。”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压制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发展相对缓慢。而商品经济的兴盛与封建皇权的集中,却使中国商人走出了一条夹缝求生的道路,既充满矛盾,又自成一体,凝结成“商帮”这一极具特色的商人组织形式。

何谓商帮
从字面意义上看,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含义是为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清裨类钞》中记载 : “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自封建制度确立以来,历代统治者不断对商品经济进行控制与干预,同时利用文化思想加以限制,使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阶层中屈居末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商”并未因为统治者的不提倡而断绝,丰厚的获利仍然引诱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与投机,在民间,丰富的贸易活动灵活地填补着官营工商业的空白。
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名城,出现了“柜坊”“飞钱”等金融业上的创新。两宋时期,由于商业政策的宽松,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为交易提供了便利,商业赋税逐渐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在明代之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大多是单个的、分散的,也即“有商而无帮”。明清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群体日益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才出现了这种商人结为“亲密”又松散的群体的现象。
研究者将商帮定义为: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公认的十大商帮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洞庭商、鲁商、江右商和陕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地域性商人出于同乡之谊也会有互相帮助,但没有正式组织,即不能称为“帮”,如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因此,笔者认为“商帮”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二是以会馆、公所作为有形的联络载体。
作为地域性商业联盟的商帮,严格意义上只限于明清两代间,是封建社会末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上,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显示出“成也官,败也官”的特性。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这些商帮多遵循血缘和宗法纽带,信奉中国传统的“诚信”“仁义”“和合”观念,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其中不适应时代的因素,又阻碍了他们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领域中更进一步。
商帮在明中后期诞生后,依附于封建制度,随着封建社会逐渐发展至顶峰,同时也迫近了落日的余晖。至清代末期,由于清廷政策的变化,兵祸战乱,以及西方商品冲击我国封建商业体系,商帮的存在已经名存实亡。清代灭亡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束,曾经煊赫一时的明清商帮,终于风流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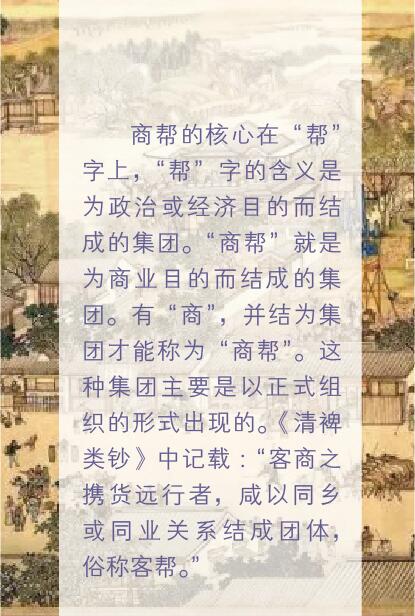
应运而生
各地商人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自发结成以地域为中心的群体进行活动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明中后期。为何在明代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集团?一方面,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人群体日益壮大,封建社会发展至此,出现了诸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现实因素,为大规模长途贸易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在官营手工业衰落的同时,民营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各地产品结构的差异性,为商人成帮经营提出了现实要求。
明代继元而兴,山河一统,幅员阔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无不来庭”,为大规模的商品运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为了运送漕粮,明廷于永乐年间重新疏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为了巩固边防,又在北部修建了许多道路,以输送粮饷辎重。在粮饷官物便捷运输的同时,数量可观的民间商品也奔流在通行无阻的交通干线上,构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明代交通之便,正如宋应星所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明初各地尚以实物缴纳赋税,而正统年间产生的“金花银”,即将实物折算成银两缴纳赋税,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很快便流传开来,使白银成为大规模流通货币有了可能,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白银的逐步货币化改变了传统支付手段,提高了结算效率,史料显示,白银货币化的时代,正是各地商帮先后产生的时代。
此外,明中期开始了一系列赋税、徭役的改革,加大了田产在赋税中的比重,减轻了人丁的负担,无地的商人由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免除了力差,实际负担有所减轻,工匠也可以银代役,商品劳动人手增加了。明代征收商税“俱三十税一, 不得多收”。总的来说,商业税率较宋元时期偏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商税负担摊入田亩,也必然驱使更多农人转入商业活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社会上对商人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成化、弘治时注重经世之策的大学士丘濬说: “今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在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看来,天下人就算不从事商业,行为也与商人无异,足见经商已经蔚然成风,商人实际社会地位并不卑下。
在一些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抑商观念薄弱的地区,重商思想与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互动。在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士子们有意或无望地转向经商之途,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士商的交游甚至互流都不再罕见。在宗族观念较强的徽州,随着同村、同族从商者的增多,许多家族甚至将经商作为维护宗族声名地位的手段,鼓励子弟出门经商。
几千年来儒家不能并行的利义观,到此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松动,由“利义离”到“利义合”,儒学渐渐转向入世价值。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主张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对正在昂首踏上历史舞台的传统商人们而言,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起于毫末
清道光16年(1832年),13岁的胡顺官走在崎岖的徽杭古道上,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到杭州去当一名小伙计。这名瘦小的徽州少年,就是后来的胡雪岩。徽谚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明清时期名留青史的富商巨贾,常常出身于贫穷的山村小镇,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在“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地狭人稠,人地矛盾极为突出,为了谋生,行商走贩成了一代代人的无奈选择。无独有偶,在晋商、陕商的家乡,也是耕作土地少,土地瘠薄。浙江和江苏土地肥沃、相对富裕,山东、河南农耕经济基础较好,但考察商帮的诞生地,分别在本省都是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反观那些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经济富庶的府州,在明代就没有兴起商帮。
然而各商帮的兴起地,大多又盛产土特产品,例如,徽州虽然粮产有限,但名优物产却非常丰富,山区盛产竹木、杉木,山间田地盛产茶叶,还有制瓷原料白土,以及手工业品纸、墨、笔、砚等,都以质优名扬全国。其他省区情形大类相同,江西瓷器举世闻名,还盛产木材、炭、苎麻等;浙江宁波、绍兴等地,有鱼盐之利;山东盛产棉花、梨、枣;河南盛产棉花、药材、染料;山西、陕西多红花等染料、动物毛皮等。
南北贸易,以有易无,各地优势物产不同,又有不同的缺乏和需要,使得当地商人有可能借助地理差异、价格优势而获利。内陆商帮,大多就是从长途贩运活动中发家的。
凡有高额利润处,就有商帮集结产生的空间。粤、闽两地临近东南大海,长期受到台风水患的袭击,传统的农业耕作不能维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早在16世纪初,潮、汕的商人就大批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亦商亦盗起家。明廷实行海禁政策,片板不能下海,但严禁无法阻止迫于生计出海的沿海居民,福建商帮就是在明正德、嘉靖年间与日本的大规模走私贸易中兴起的。
航海需要有人手,要有资财打造船只,还要躲开官军的排查,这就要求违禁走私的海商同舟共济以避免风险。随着海禁政策的部分开禁,商帮同时从事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规模更大。丝绸、瓷器、书籍等江浙一带的商品,通过澳门、马尼拉等的中转,源源输出到南洋甚至欧美等地。《五杂俎》描述当时海商通番盛况:“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
推波助澜
除了社会因素的便利与地缘因素的诱导,商帮的兴起,还与封建王朝的权力“指挥棒”有紧密的联系。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曾经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对中国商人阶级的考问,也同样精准地打到了明清商帮的痛点之上。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晋商延绵500多年的辉煌由盐商开启。作为最早的晋商主体,山西盐商正是发家于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和率先在山西开展的开中纳粮的盐业政策。
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原人杨宪向朱元璋建议在大同实行“开中制”。“开中制”的初衷是,官府向边区调运粮食路远费烦,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可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这些盐被允许到指定的区域贩卖。在这个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在中国历史上,盐的产销一直由国家控制,受到官府的严格管理,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引”就相当于政府发给商人的食盐运销许可证。在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商人自愿纳粮,政府就发给一定量的食盐经营特权,这其实是一个整合国家和商人资源,优化配置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纳粮获得盐引是关键,因此得到地利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就近屯种粮食上纳。
山西自古是食盐的一个大产区,一批大盐商在此间悄然萌生。同时,由于地处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带,拥有农牧业经济区域互通有无的天然地利,依靠贩运盐、粮食、铁农具、丝茶、棉布、草料等军需品,晋商迅速发展起来。
弘治年间,出身徽州的户部尚书叶淇在徽商的呼声下进行变法,改边境纳粮中盐为运司纳银中盐,把向边境纳粮改成缴纳银两换取盐引,不需要向边关纳粮了,为徽商挤入淮、扬的食盐专卖生意提供了机会。距离淮、浙等地更近的徽商打破垄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两淮、两浙盐业中坚。
面对徽商的崛起,山陕盐商为了在激烈竞争中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徽州盐商展开了相互颉颃的长期抗衡,他们各自结帮的意愿更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官府给予的垄断经营权对民间商人的重要性。明代还实行过“中茶法”,即商人按一定比例交茶,剩下部分可以自营,同样催生了一批拥有数十万、数百万财富的大茶商。
不可忽视的是,商帮虽然诞生过大量富可敌国的耀眼巨子,可以施加于官场甚至权力中央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但攀缘于封建权力的中国传统商人,始终受制于封建权力的制约和摆弄。随着封建制度日薄西山,各地的封建性商帮也纷纷盛极而衰。
“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费正清以犀利的洞察力写道。是“更好的捕鼠机”,还是“捕鼠的特权”,要回答“费正清之问”,还须看今日的中国商人。